在“三只手”上跳舞:公共政策的科学与艺术——读《市场、国家和民众:公共政策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在《国富论》中把“市场”传神地隐喻为“看不见的手”;一个半世纪后,面对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另一位也足够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大声疾呼“看得见的手”责无旁贷;如果再加上位于上述两手之间的民众“勤劳的手”,“三只手”便聚齐了。公共政策如同一个舞者,在这“三只手”上跳舞。“三只手”始终都是动着的,舞者平衡感的寻得,建立在对“三只手”本质的认知与把握之上,既需要科学,也需要艺术,这是剑桥大学的公共政策讲席教授黛安娜·科伊尔的《市场、国家和民众:公共政策经济学》一书所直面的挑战。
黛安娜·科伊尔可谓经济学家中的顶流,不仅拥有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是大英帝国勋章的获得者,10年前便和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一起入选英国《展望》杂志评选的“世界思想家50人”。扎实的经济学训练,叠加躬身入局直接参与多项重大政策制定的亲身经历,使得本书能够将在“三只手”上跳舞的公共政策,置于宏阔的历史与经济、社会背景中,“既充满智慧,又视野广阔”,远在哈佛的另一位顶流经济学家格莱泽教授也忍不住赞叹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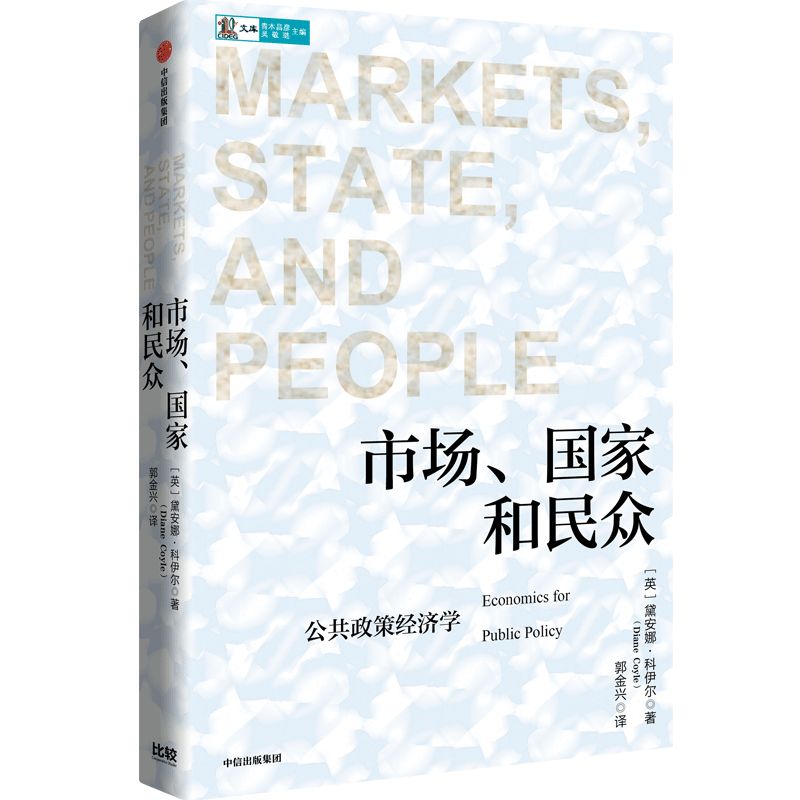
一、公共政策舞者脚下的“三只手”
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资源配置与分配,即“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效率是经济学家讨论上述问题的准绳:供给侧的资源是否有效地转化为了产品,产品是否符合需求侧消费者的偏好,供需匹配过程中产品是否被提供给了出价最高的人。效率,也是民众“勤劳的手”孜孜以求的。人们这样勤劳,为的是自己,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先满足他人。如同斯密深刻地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利己和利他不仅不冲突,还在平等交换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如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
这只“看不见的手”便是市场,价格充当着那神奇的指挥棒,高效地协调着人们的意愿与行为。作为消费者,偏好不同不要紧,价格可以协调;作为生产者,成本不同也不要紧,价格也可以协调。价格之所以能胜任这一角色,是因为其可以发现并汇总分散的信息,这一优势是独一无二的。解决了信息问题,激励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
价格也有指挥不好的时候,这便是市场失灵,典型的场景是当有外部性存在时,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就需要来收拾局面,通过“命令”来进行协调。通常来讲,“看得见的手”主要提供具有外部性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但大萧条、二战及战后的大规模重建,使得“看得见的手”的协调范围极大地拓展了,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东亚的日本,民众“勤劳的手”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看得见的手”的力量。
实事求是地讲,“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并不截然两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决定了其配置资源有效性的边界,关键看哪只手可以让民众“勤劳的手”以一种交易成本节约的方式保持勤劳。公共政策在这“三只手”上跳舞,交易成本实际上便是那舞步挪动时的摩擦力,交易成本节约也理应成为公共政策科学性的标尺。
二、事件和观念:舞者节拍的“快”与“慢”
黛安娜诚实而深刻地指出,“我们面临的是无法避免的困境或妥协,没有什么政策解决方案能够永远正确且放之四海而皆准”。换言之,在“三只手”上跳舞,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保持良好的节奏感就至关重要。真实世界中,公共政策之舞节拍的“快”与“慢”是事件与观念的产物。
重大的危机事件往往能驱动公共政策快速的应激性转向。两次全球大危机加强了“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大萧条驱动了公共建设与社会保障大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则推动了对金融监管的反思与调整。但复盘来看,上述快速调整与危机应对所需的最优的“快”相比,总还是慢一拍。这是因为,危机爆发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使得公共政策决策者在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错过时机。此外,斯密为“看不见的手”吹响号角,也是工业革命这一重大事件驱动的,此时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的诸多管制有利于既得利益者,而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与社会的巨大变革呼唤更加高效的协调方式。
观念是对因果关系的认知,其公共政策影响则是相对缓慢的,但往往更加牢固。“思想观念散播出去的时间与它们支配行动的时间存在着间隔”,哈耶克认为,“通常会长达一代人的时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也深刻地指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充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实际上,大多数人30岁之后便很难接受新的观念,所以公共政策决策者所依据的观念不太可能是最新的。换言之,观念隔代产生影响是常态,这一时代的公共政策,或许正好是受上一时代观念影响的人成为决策者后的实践。此外,观念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很多时候是自上而下的,“一位巴黎的时装设计师,虽然他的时装只有少数几个买家,但是却能影响几乎所有的流行时尚”,很多顶级智库的政策研究报告往往也是先影响决策者的观念,然后才可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三、“助推”:公共政策科学中的艺术
基于理性与自利的行为,是传统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然而,真实世界中,具体而真实的人对理性的偏离,有可能使个体决策产生的经济后果偏离经典的效率框架。例如,明明知道下次站上体重秤时会后悔,仍然选择在夜深人静时大快朵颐,“理性人”的标准假设,并不能正确地预测并解释这些“错误”的行为。
公共政策舞者的舞步,也需要随之进化与迭代,基于大量心理学研究的行为经济学及时地提供了良好的补养。“助推”,便是那进化后的舞步。行为经济学根据一些经验法则,对决策行为进行分类,如过度自信、厌恶损失以及锚点、框架效应的影响。锚点与框架效应,说白了就是“选项”的呈现方式会直接影响人们的选择,塞勒等研究上述“错误”的行为的经济学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是“助推”这一公共政策新舞步的理论基础。
“助推”最著名的公共政策实践,是将美国退休金储蓄账户的默认选项改为“自动加入”,即以默认的储蓄率、默认的投资方式加入退休金计划,而不再需要员工额外填表来选择储蓄率与投资方式。在这一政策的“助推”下,新雇员的养老金计划参与率提高了50%。这背后其实还是“交易成本”在起作用,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填写表格和敲定投资策略都令人生厌甚至生畏,需要付出不小的“交易成本”,而将加入退休金计划设为默认选项则会容易很多。可见,“助推”理念用得好,公共政策之舞也就更加优美。
以上这些闪闪发光的洞见,仅仅是《市场、国家和民众》这本公共政策教科书中的几个美丽的贝壳,这是同样作为公共政策研究者的我拾出来的;更多的更美的贝壳,还需要意犹未尽却又偏好各异的广大读者们自己去拾取。
(王瑞民,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