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陈海贤:在这个时代,找到自己的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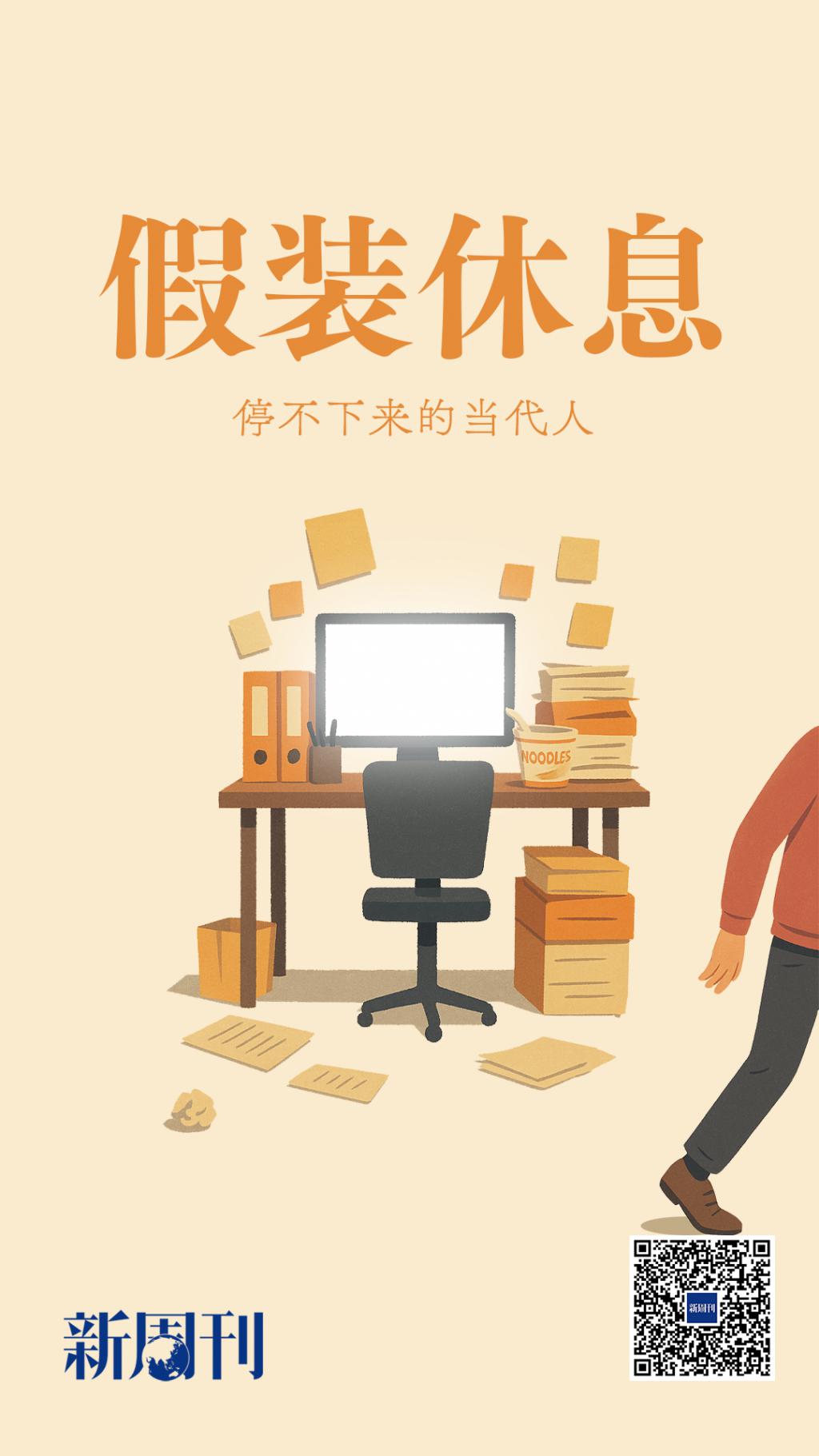
现在网络上很流行 " 不婚不育 "" 不买房 " 等现象,其实这些新的生活方式都很 " 轻 ",是另一种虚无主义。
作者 | 段志飞编辑 | 宋爽在进入 " 试着休息 " 这个话题之前,我与陈海贤对于 " 休息 " 的理解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作为一个当代年轻人,对于我来说,似乎只有工作之余是我唯一能想到需要休息的时候,但在陈海贤看来," 不得不做 " 的工作,并非痛苦的源泉。为了自洽,我只好暗自认领了自己的肤浅。
大多数年轻人是不太爱听人讲大道理的,除非 " 听 " 和 " 讲 " 的位置调换过来;他们也表示对于心灵鸡汤早就脱敏,但其实这也取决于话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只不过有的鸡汤不咸不淡,而有的则经过了审美的包装,被调配得更合口味了。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听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提到自己 " 需要看心理医生 "。其实能够想象,从少年到青年,从校园到社会,我们似乎被卷入了一个庞大的机器,成为其中的一枚齿轮,除了要面对煎熬的工作、总是轻易断掉的关系、一成不变却迷茫的生活以及那个始终不如意的自己以外,当外界环境的冲击和变化与 " 我想要 " 并不匹配甚至矛盾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这恐怕是当下每一个年轻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这一切真的有答案吗?我问陈海贤,而他的回答是——答案不在你的头脑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像手术刀一样割开了我眼前的迷雾,原来最简单的道理并不需要高级的词汇去包装。后来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把自己当成一个 " 病人 " 完全交给他。聊完之后,好像自己也完成了一次疗愈。
今年 3 月,陈海贤的新书《走出黑森林:自我转变的旅程》出版," 黑森林 " 隐喻着现代人的心理迷失。继《了不起的我:自我发展的心理学》之后,他始终在关注个体的 " 真实困境 "。
以下是《新周刊》与陈海贤的对谈。

越过于强调自我,
越可能使自己孤独
《新周刊》:我们经常能看到人们用 " 年轻人的选择 " 来形容当下社会的体征。关于 " 年轻人 " 的定义其实范围越来越宽泛了,在你看来,当代社会的年轻人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
陈海贤:用 " 迷失感 " 来形容应该会比较准确。我们会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不知道该怎么预期。确定性连接了 " 努力 " 和 " 可能得到的成果 ",它构成了我们生活最基本的秩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追求关于人生 " 该怎么活 " 的更多意义。
现在年轻人意义感的缺失,使得他们开始孤立自己,觉得所有事情的终极意义都不存在了——工作只是为了获得报酬,而两性关系里双方都觉得委屈,这些都导致了年轻人将自己孤立起来,以及对待工作和感情不投入。" 不投入 " 带来的空虚和迷茫感成为年轻人很明显的特征,所以现在网络上很流行 " 不婚不育 "" 不买房 " 等现象,甚至还有一些反常规的生活方式。其实那些新的生活方式都很 " 轻 ",是另一种虚无主义。

陈海贤。(图 / 受访者供图)
《新周刊》:关于生活的秩序感,会让人想起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正向反馈,只要敢拼敢干,基本上都能获得成功,但是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变了。你怎么看待当代年轻人心理的异化?
陈海贤:这个问题需要结合社会学和历史学来看。" 异化 " 通常指的是人在某种程度上被 " 工具化 " 了,比如说你的情感、自我、思想,统统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对社会所起的作用。" 异化 " 还有另一种理解,那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 原子化 ",现代生活让我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有权利强调自我,而强调自我反而让大多数人越来越不知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维持某种长期关系,甚至不知道如何锚定自己在社会上的坐标。
至于你提到的过去那个年代,我觉得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面临 " 寻找意义 " 的任务——跟谁结婚?组建什么样的家庭?怎么过一辈子?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迷茫和不确定性。当代年轻人的难题在于,因为外界的不确定性增多,所以他们只能转向内心去强调自我,而过于强调自我,也让大家开始觉得 " 我可以不用完成这些任务 ",这也是当代年轻人比较主流的心理趋势。
《新周刊》:年轻人强调自我的同时,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不顺利,也很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 " 抱怨 ",一种是 " 自责 "。怎么去调整这些心理?
陈海贤:先说自责。这种情绪的由来,通常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存在严厉对待我们的人或压抑的环境,比如父母、老师或者周围社会的评价标准。在我们很弱小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要符合他们的期待。等到长大了以后,这些声音逐渐变成了我们的声音,甚至很难去掉。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一部分人会过于倾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还有一部分人则过于容易将情绪转移到外部环境,这两种其实都是比较偏执的。
你看,我并没有给你怎么去调整这些心理的答案,但是找到这些情绪的由来至关重要。实际上心理学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不只你这样。而社会学的作用就是:这不是你的问题。有时候我们需要综合地看待那些不顺利。

去努力,而不是假装在努力
《新周刊》:现在大家普遍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可能因为社会结构性造成的一些困境,比如全球经济下行、各种价值观冲突等,都使得社会面临变化。在你看来,年轻人怎样重建个人的秩序感?
陈海贤:一个东西悬浮在空中,是因为没有连接大地的根。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的根基,哪怕外部世界变动再大,也能让我们内心保持相对的稳定呢?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牢靠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一般是由家庭提供的,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来自能够信任和接纳我们的朋友或恋人。很多年轻人因为很难得到,甚至害怕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所以就会产生悬浮感。其实传统的、建立在长期主义之上的亲密关系的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被低估的。

(图 / 图虫创意)
第二种根基,就是 " 我会什么 "。也许不是扮演某个角色,也不是迎合某个社会组织的要求,而是当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会觉得踏实,能够对自己的能力给予肯定。如果再往外拓展,那就是 " 我能决定什么 ",比如我能决定我在哪座城市,决定自己从事什么职业,这些都能成为我们根基的一部分。
《新周刊》:很多年轻人都不爱听大道理,会觉得 " 道理我都懂,但是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关于 " 做不做 ",是不是因为我们本能地会害怕失败?对于许多具有不可抗力的事情,就算尝试去做,是不是也会变成一种无效的自我安慰呢?
陈海贤:我们对很多事情都习惯性以为靠想就能有答案,但其实很多时候靠想是想不出来的。小时候学钢琴,老师就已经教了我们这个道理,所以 " 想 " 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想实践又害怕失败,那怎么办呢?
我之前提出过一个原理叫作 " 小步子 ",就是把自己的目标一步步地具体化到可以去行动为止。比如我不知道怎么找工作,那我至少先做份简历;如果不会做简历,那至少先打开电脑和 Word。很多人会问:做了这些行动真的有用吗?我就能找到工作吗?这个时候我会回答他们,行动或许不一定有结果,但一定能创造某种可能性。
如果他们接着问,这样会不会成为自我安慰,那我想说的是,从理论上来讲,只要行动就会有反馈,而安慰是指寻找证据证明自己在做改变。这里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弄清楚,那就是:你是想通过行动这个步骤,为了创造某种可能性而尝试,还是为了制造 " 我在行动,我在努力改变 " 的幻觉?
如果是前者,那很好,你已经在行动了;如果是后者,那你确实是在自我安慰。不过话又说回来,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努力,以及模仿很努力的样子,这两者的本质区别其实在于,你是否明确了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找工作,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非常渴望一份工作。

别把努力和休息当 " 应该"
《新周刊》:" 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下 ",该怎么选呢?
陈海贤:其实可以换个角度来看 " 休息 " 和 " 内卷 ",卷不动又躺不下,所以就成了 " 仰卧起坐 ",但仰卧起坐好歹也是一种对身体强度的锻炼。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自己:我有资格休息,如果我要为自己重要的目标而努力,那就去卷一下。所以 " 休息 " 和 " 内卷 " 也有好坏之分。
那些 " 不得不做 " 的工作,的确会成为我们内心当中巨大的矛盾,但是那又怎么样呢?送外卖很辛苦,可是如果不做这份工作就没有饭吃,那还谈什么想与不想?所以 " 你要怎么办?" 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也不是《新周刊》能回答的问题。人要面对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去解答。这个不是考试答案,而是我们对人生负责的一种态度。
《新周刊》:你觉得最好的休息是什么?
陈海贤:很多人觉得没有精力,是因为他们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克服对 " 不得不做 " 的事情的厌倦上,如此才会觉得消耗,就算躺一会儿,让身体休息了一下,但精神上还是焦虑的。

(图 / 图虫创意)
我觉得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最好的休息。除了那些 " 不得不做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情。我的休息就比较大众,比如做一些简单的冥想、睡一个 20 分钟的午觉、抽出一段时间独处读书,或者喂喂鱼。只要去做让自己放松的事情,就能起到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新周刊》: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怎么思考都觉得很难找到答案的事情,其实关键在于去做一做。休息也是一样,去试试,说不定真的有用。
陈海贤:以前励志文化盛行的时候,大家喜欢说 " 我要改变 "" 变成更好的自己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说过,不要把转变和努力当成一种 " 应该 ",好像没有努力就是不对的。
同样地,我们也不要把休息当作一种 " 应该 ",好像没有休息的生活就是坏生活,我觉得不是。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审视它,并且做出选择,所以无论是休息还是奋斗,只要是在做自己,那就是自洽的,没必要拿外界的标准来界定好坏。
另外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一定会有很多外在的现实告诉你,你要这样,或者你要那样,年轻人对此会有两种态度,要么顺从,要么反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是不是也存在第三种态度?那就是在做选择的时候,把自己的自主权找回来,告诉自己:我既不是顺从别人,也不是别人要求我要反抗,而是我自己内心真的想要。
《新周刊》:在《走出黑森林》的后记中,你提到 " 穿越黑森林是生命最珍贵的礼物 "。若要对正在挣扎的年轻人说一句话,你会想说什么?
陈海贤:你不是你遇到的事,你是你选择成为的人。